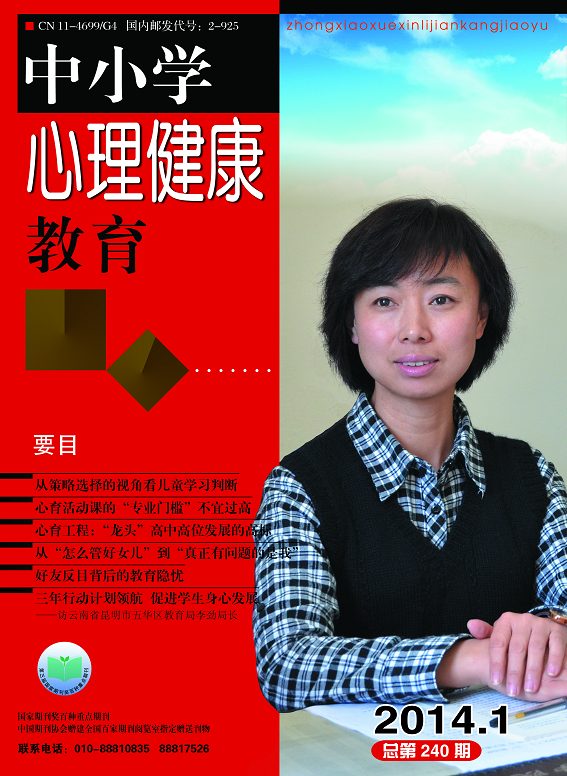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关键是来访者与心理医生的关系品质,要形成一个好的关系,心理医生与来访者都需要学习真诚。
经常有读者写信给我说,他们的心理医生让他们如何如何不满意,他们该怎么做?
我的回答一律是,与你的心理医生谈谈这些不满意,并且,越真诚越好,越直接越好。
这样回答,既是一个心理咨询的原则,也是我自己做心理咨询的体会。
武老师,你太自恋了
完美的心理医生会有非凡的洞察力,他们能敏锐地捕捉到来访者种种微妙的心理,而能发现来访者的不满,并与来访者直接探讨他们的不满,从而促进咨询的进展。
但是,也可以说,所有的心理医生都在路上,完美的心理医生不存在,期待一个心理医生能够时时刻刻地觉察到自己的状态,并且能时时刻刻令自己感觉到满意,这是不可能的,而且这其实是婴儿时的心理状态的再现。
实际上,当来访者感觉到不满时,这经常会是一个关键时刻,假若他能敞开心扉,与心理医生主动说出不满,那不仅会促进来访者的成长,也有可能会帮助心理医生成长。
在这方面,我有深刻的体会。
在做咨询半年多后,我有一位女性来访者F,她有非常敏锐的感觉,常常能捕捉到我的感受,在这一方面,她比我厉害。
那时,我才开始使用身体聆听,对这一点有些着迷,也有些自恋,因太多时候,我发现,对方有什么感受,我的身体就会有相应的感受,身体如此直接,身体似乎从来不欺骗自己。
一次咨询中,F犹豫了很久后对我说,武老师,我有一个不好的体验想与你分享,希望你不要介意。
哦,欢迎,我说,在这个房间里欢迎你说出一切。
她仍然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,武老师,我觉得你太自恋了,你那么喜欢用身体来聆听,你总是说你的身体有什么反应,并反问我如何,那时候,你看上去沾沾自喜,好像很期待我给予肯定的回答,这给了我很大压力,所以我每次都会回应说,是的,我一样也有类似的反应,有时我还会说,你真的很敏感很厉害。但实际上,很多时候,我不是这样子的。
她这样说,令我有些震惊,我完全没有想到,过去她给我的回应,都是用来讨好我的。我停下来,不说话,而是好好回忆并体会过去使用身体聆听的一些时刻,我发现,自己的确有沾沾自喜的成分,而且这个分量还比较重。
于是,我向她承认,我发现自己的确很自恋,当得到你或其他来访者肯定的回答时,我心中会有一点沾沾自喜的满足感,觉得自己很棒。
然而,听到她说,过去她一直都是在迎合我,这令我感到难过,也感觉到有些遗憾。
我继续对她说,我觉得,我是有沾沾自喜的部分,这部分还蛮明显,但我觉得,如果你能直接对我说,武老师,我的感受不是这样子的,那么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受伤。
最后,我也反问她,为什么我的沾沾自喜给你那么大的压力呢?这会让你想到什么?
她想了想说,这和她与父亲在一起的经历有关,这也和她与其他亲人在一起的经历有关,很小的时候,她就学会,通过捕捉对方的感受,去发现对方的需要是什么,然后去满足他们,那时他们就会很高兴,并因而更加喜欢她……
经过这次谈话后,我感觉,她在咨询室中变得轻松了很多。
同样,这次经历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,后来我总结发现,在很多时候,我使用身体聆听时并不准确,所以,我在使用身体聆听时会加一句:“这是我自己的感受,未必是你的,你的感受是什么?”
治疗技术是第三者
弗洛伊德是迄今为止最有名的心理学家,但多次调查显示,对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的影响,弗洛伊德排名第二,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排名第一。
心理医生之所以会将罗杰斯放到第一位,主要是因为罗杰斯提出,心理医生与来访者的治疗关系,才是心理治疗的核心因素,而心理医生的真诚、温暖与无条件积极关注,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因素。
现在,几乎所有的心理医生都会知道,他们与来访者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。
不过,很不同的一点是,相当多的心理医生会认为,心理医生与来访者的关系是基础,理论知识与技术更为重要。而在罗杰斯那里,关系就是一切。
我倾向于罗杰斯这一边,在我看来,心理咨询与治疗中,技术很重要,但技术更像是一个第三者,心理医生要借助这个第三者与来访者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,而比说什么和做什么更重要的,是心理医生与来访者的关系素质。
这一点我早在大学本科时就坚信无疑了,但能打心眼里体验到这一点,是得益于一位来访者K。
K的收入有限,他差不多是一个月来找我一次。他对我抱着很大的期望,希望我能赶快将他从问题状态中拉出来,我一方面受这个期望的影响,同时自己也希望加快疗程,早早帮助他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会适应能力。
为此,我在他身上使用了种种治疗技术,如精细的自我解梦、催眠与NLP等。尤其是两次解梦,我觉得精彩异常,甚至因而开始期待,他的心门该因此而开了吧。
但是,他的心门迟迟没有打开,咨询做了约一年后,他仍然觉得没有什么进展,中间还暂停过两三个月时间。
精彩的技术没有带来突破,反而是,他后来做的一件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事情带来了突破。
一次,他对我说,武老师,我一直瞒着你一些事情,我总是希望不讲这些事情就可以取得进展,但我想,也许讲讲这些事情会对我有帮助。
说了这些话后,他仍然是犹豫了很久,才终于给我讲了他隐瞒的事情。
他讲出来的事情令我震惊,但震惊不是因为这些事情太特殊,而是因为,这些事情在我看来太平常了,如此平常的事情,却成为他不能承受的重担,我觉得实在是有些难以理解。
我将我的这些感受告诉他。并且,他本来非常担心我会因为这些事情对他有很不好的看法,我则承认,这些事情的确我会有些看法,但假若完全觉得这是好事是0分而完全觉得这是坏事是10分的话,那么我的看法也最多不过是6分。
更重要的是,即便我对他做过的这些事情有看法,但这些事情本身在我与他的关系中就没有太多分量,这些看法影响不了我与他的关系。而且,我分明感觉到,当他讲了这些事情后,我与他的关系亲近了很多。
这次谈完话后,我感觉他明显放松了一些,而接下来的一次咨询中,他有了一个很深的洞见。他说:
一直以来,我觉得自己不够好,必须改变。因为这样的看法,我不敢与别人交往,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,觉得这是确定无疑的事情——我真的不够好。但现在,我走出来了,我才发现,我并不比别人差,实际上,我的确有不少蛮不错的品质。发现这一点后,我坦然了很多。
因这个洞见,他的自我接纳程度高了很多,或者说,他的自爱高了很多,而自爱,也许可以说是心理咨询的终极目标。
直接说,我还不够信任你
K的故事显示,哪怕仅仅向心理医生袒露自己,有时就会带来很好的疗愈效果。
这是为什么呢?
我的答案是,一个人之所以不敢袒露自己的某一方面,是因为他将这些方面视为“坏我”,而“坏我”其实是在原生家庭那个很小的世界中形成的。当父母向孩子传递一些信息——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,如果你这样做,我们会不喜欢你疏远你甚至想与你断绝关系,孩子的“坏我”就形成了。“坏我”的核心是惧怕失去别人的爱,“坏我”形成时的逻辑越严厉,一个人的内心就会绷得越紧,因为这种紧张,他会发展出种种心理问题。
当孩子长大成人进入社会后,他还会不自觉地认为,这些方面是别人绝对不会接受的“坏我”,他绝对不可以呈现出来。但实际上,现在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原生家庭的人际关系网络已大不相同,原来那一套心理逻辑已不适用了,依照美国心理学家斯考特•派克的说法,这个人就应该修正其心灵地图了。
K与我的关系,即是一个新的人际关系场,他将那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事情隐瞒了一年之久,那是因为,他并没有活在这个新的人际关系场中,他的心仍然停留在原生家庭的场中。但是,只要他一呈现这些事情,他便会发现,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场,他完全不必执着于原来的逻辑,于是,他松动了自己那一套苛刻的心理逻辑,他的改变也由此自然发生。
什么是心理健康?在我看来,灵活与宽容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。你可以这样你也可以那样,这就是灵活与宽容。相反,僵硬与苛刻即你可以这样但你绝不可以那样。不过,这还不是最糟糕的,最糟糕的是,你既不可以这样也不可那样。
类似K这样的故事有很多,我发现,太多时候,仅仅因为来访者向我袒露了什么事情,治疗效果就自然发生了。
不过,治疗效果的发生有一个前提,即在心理医生与来访者的关系中,真的是有这样的氛围——“你可以这样,你也可以那样”。假若心理医生自己心中都有着很多苛刻的教条,那么这个效果难以自然发生。
如此一来,作为来访者,就面临着一个选择——我要不要向心理医生袒露我的内心?
我会说,相信你的感觉。如果你能感觉到你与心理医生彼此信任,那么就去袒露你的内心。
但这又是一个新的矛盾,因为信任其实是逐渐建立的,虽然有的心理医生会容易给人信任感,但真正的信任感总是逐渐建立的。
那么,具体该怎么做呢?办法就是,去和你的心理医生谈你的感受,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。
譬如,你感觉,尽管咨询做了很久,但你仍然不够信任他,那么你可以和心理医生探讨这一点,对他直接说,我直到现在还不能信任你。
这时,合格的心理医生会和你比较中立地去探讨这种不信任感,假若一个心理医生因而感觉到很大的受伤感,于是顾左右而言他,或者干脆说,这肯定是你的问题,那在我看来,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心理医生。
心理医生的很多“不良反应”是对来访者的呼应
很多时候,不信任感是具体而发生的,譬如很多读者在来信中均写到,在咨询中,他们的心理医生会走神、打呵欠甚至打瞌睡,这让他们感觉很不好。
对此,我的建议一律是,去和你的心理医生说,某次咨询时,你走神、打哈欠甚至打瞌睡了,我感觉很不好。
咨询室中发生的一切都有意义,走神、打哈欠、打瞌睡乃至睡着都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。
一次,在我的课程“自我觉醒之路”上,一个学员分享她的心得,我听着听着就走神了,发现后赶紧把自己抓回来,但听着听着又走神了。于是,我和她分享说,我发现,听你讲话时我总是走神,这在今天真是罕见,我之前听别的同学讲话时注意力是非常集中的。
这名学员说,她也注意到我走神了,有点不快但没有多想,你这样一问,我才想起,刚才我和你说话时,我的眼睛一直在瞟着左侧的墙。
我请她感受一下她的身体,她感受了一会儿说,她感觉到心口好难受,呼吸变得很困难,刚才就有这种感受出来,但那一刻她感觉到害怕,所以把注意力转移了,看左侧的墙,说一些大道理,就是在逃避这种感受。
这个例子显示,作为老师,我的走神是对她的走神的一种呼应。
在咨询中,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。除非是,我自己远远没休息好,很累,那时的走神、哈欠、瞌睡是自己的原因,否则基本上都是我与来访者之间的一种呼应。
因而,当我有走神、打哈欠、打瞌睡甚至睡着的情形发生时,我都会主动告诉来访者,刚才发生了什么,并与他探讨。
有时,我会等待,看看这些情形什么时候会消失。
前几天,一次咨询中,听一名男性来访者讲一些事情时,我困得厉害,稍一闭眼就睡着了。我向他坦承了我很困,之后我们继续进行谈话。过了一会儿,突然间,我感觉困意消散了,接着,他和谈起了关于性的问题。
就此,我们进行了一点探讨,我发现,那种困意,是我感应到了他对性的压抑。
这是很微妙的一点。当他想谈性而不好意思时,作为心理医生,我的感觉是困极了。这是我的反应方式,如果换一个别的心理医生,他可能会有他自己的呼应方式。比方说,他可能会变得极其兴奋,会有一种想追根问底的冲动。
由此,可以说,心理医生有什么样的呼应方式,既反应着来访者的特点,也反映着他自己的特点,所以,如果可以就这些进行及时的探讨,不仅对来访者会有帮助,对心理医生也是一种治疗。
相当多的时候,我会发现,来访者之所以不敢袒露一些事情,其根本问题在于性,可能一开始的表面问题是别的,但最后会发现,多是围绕着性所产生的负罪感乃至罪恶感,令自己不敢袒露心声。
还有相当多的时候,不敢袒露是因为太痛苦了,就像我那位女学员,她那种不能呼吸的感受是强烈的被抛弃感,多年以来她一直不敢碰触它,因为一旦碰触它似乎会有排山倒海的力量,会冲垮自己,所以那时她要走神,要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。
也有很多时候,咨询室中的走神、哈欠与瞌睡,是因为谈的话题不是围绕着来访者的,而是围绕着心理医生的。
一天,一位来访者来到我的工作室,我们谈了约10分钟时,我也是困得不得了,问她怎么样,她说,目前谈得这个话题她觉得没什么意思,她本来是想谈另外一个话题的,但好像我对目前这个话题很感兴趣,所以她觉得不好意思转到她想谈的那个话题上。
当她转移话题,开始谈她想谈的话题后,那种困意刹那间就烟消云散了。
电影《阿凡达》中传递了一个理念——链接,战士要和六腿马链接,要和战鹰链接,而在祈祷和为人做治疗时,需要整个部落的人一起链接。
链接,也是心理咨询与治疗中最重要的,当你不敢袒露自己时,你就切断了与自己的链接,那时心理医生也将失去与你的链接,而像走神、哈欠与瞌睡,常常也是因为失去了链接。这时,心理医生也罢,来访者也罢,都需要努力,将注意力重新拉回到感觉上。
所谓感觉,就是来访者与自己内在的链接。